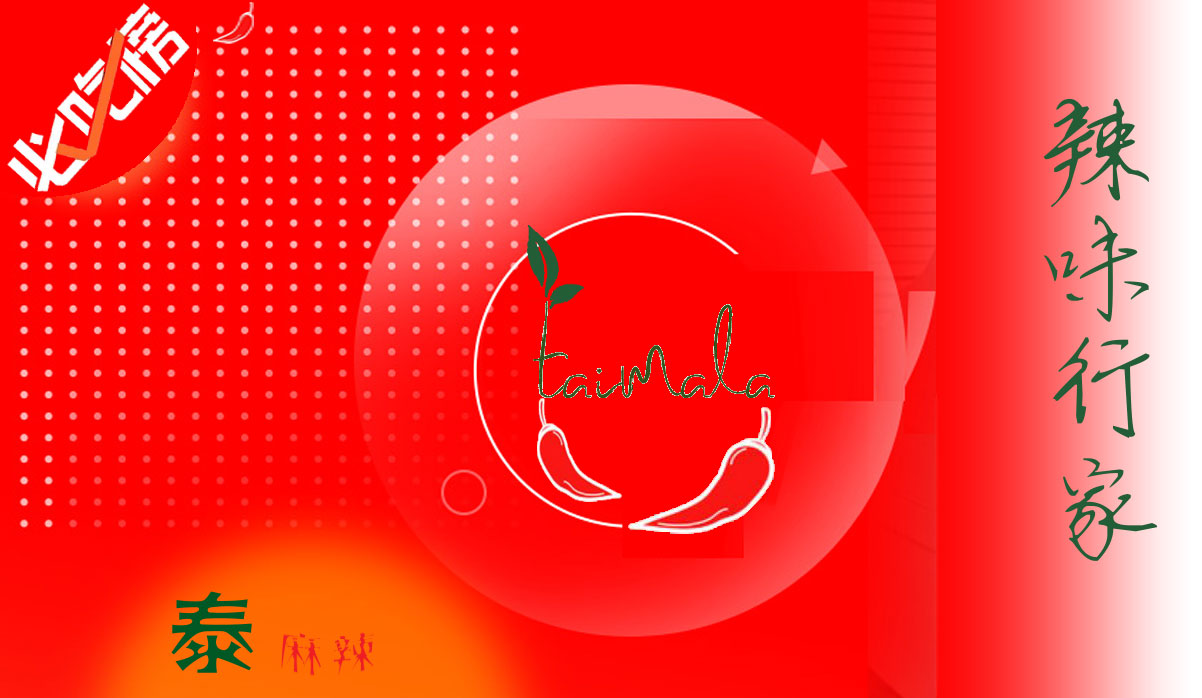女人版我命由我不由天
更新时间:2019-10-19 11:32:25•点击:26861 • 麻辣文学

如果上天有眼,那么他不该把我送到这个世界;如果上天是善良的,那么他不该让我遇到张文;如果我是个恶人,那么我不会在汤煮火烧里如此煎熬;如果我是个荡妇,那么不会有人敢扇着我的脸骂我“破鞋”! 我的名字叫泰幽幽,是三个会让人浮想联翩的字,这个名字是爸妈起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地方去问,爸妈早就死了。我也没去问过爸妈的魂灵:既然要死的这么早,为何还要把我生出来? 我在海边的城市出生,没来得及对那个城市有什么记忆,好象爸妈带我去看过军舰,我跟军舰上的一个年轻军人有过一张合影,那个军人高大威猛,头上斜戴着的帽子,后面两根飘带拂过我的脸,那个城市给我就是这些。
童年的生活象没有出壳的小鸟混沌而温暖。 好象一刹间,蛋壳在覆巢之下破掉。爸妈带我到山城看爷爷奶奶,车子在我的歌声里翻下悬崖,我手脚俱在,完好无损。当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我竟然在努力地爬过血糊糊的死人堆,钻出扭曲破碎的玻璃窗。 我的小手捧着两个骨灰盒,被领到爷爷奶奶的家,山城最初的记忆就是两个老人的哭声,在哭声里我看着门口的苦楝花不断的飘落下来,紫色的细花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让人哆嗦。那时侯我六岁。接下去的就是两个老人不断的战争,似乎奶奶总是在骂人。有时候外面买菜回来,进了门槛掼篮子就骂,基本上是骂爷爷老不死,丢人现眼,一个老干部,竟然还要在家吃老婆饭,被人笑死!骂着骂着,就动起手。爷爷一般不吭不响,奶奶动手他也会上火,但是没有回手,只是狠狠的砸掉手里的搪瓷茶缸,发出巨大的“哐啷”响声。那个搪瓷茶缸因为老是被砸,已经凹凸掉瓷的不成样子,上面“先进工作者”和“奖”字都残缺不全的佝偻着。奶奶就在茶缸的“哐啷”声里天一句地一句地哭起来。我坐在苦楝树下不停地战栗。 后来知道,爷爷的确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直在外地工作,不过也没有担当什么领导职务,一直做着一个会计,后来却被开除公职回家。一个会计被开除,人们能想到的最正常的理由是贪污。我就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是贪污犯的孙女的。那时我十几岁了吧,有一段时间大米涨价,粮站里的米脱销,每次只能买十斤。奶奶叫我也去排队,天没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真的很早,我贴着门板排在第一个。可是打开门的时候,马上有人把我挤出去,我不服气又挤回去,后面的人就大叫:“不准插队!不准插队!”粮站里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谁插队?”一个大个子声音很凶。我还在挤,大个子一把揪住我的领子,把我象一只鸭一样拎出来。后面的人都笑着说:“这个贪污犯的孙女悍辣呢!” 那天我没买到米,大个子叫我滚,说是要抓个不遵守秩序的典型,不卖给我了。我不伤心没买到米,我伤心地哭着回家,问爷爷为什么要做贪污犯? 问的结果是我被奶奶一个耳光扇到了门背后。等我知道爷爷的开除材料上写的其实是蔑视领导,不服从组织安排这样的处理意见时,已经是很多年后,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并不关心了。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遇到张文。
我的生活似乎在十八岁以后有过良好的转折,那时侯,我参加了工作,在奶奶退休前的单位——映山红制刷厂上班。我的变化不光在于我外表已经不是那个头上扎着两把刷子,任谁也可以出手来揪一下的小女孩,我留了长发,会坐一天火车到市里去烫最时髦的前刘海,我舍得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块雪青色的乔其纱做连衣裙,是这个小城里最新潮漂亮的人儿;更主要的是我已经不再可怜兮兮地害怕所有人,我会使用矜持高傲的目光温和而藐视地看人:人们,这个女孩会比你们都出众些的!
人真是十分奇怪的一种生物,当我敬重他们每一个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没有放弃狠狠地欺负我一下的机会。以前一具具庞大的身躯,令我震骇的声音,待我能和他们平视的时候,发现原来不过是委委琐琐的一群蝼蚁,有时做一些害人不利己又无价值的争执呻吟而已,我不想和他们产生对话! 一个年轻的女孩,对人有这么刻薄的认识,没有什么奇怪,“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是得了便宜卖乖,有阳光在先导,谁不会灿烂?我虽然对人们抱有鄙视的心理,但是我的态度还是谦恭的,我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至少这点,我认为我比他们高尚。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那段时间我欣赏到较多的笑脸艺术,应该说大多数人具有表演的欲望和天分,有的精湛,有的拙劣,但是很少人放弃表演。奶奶也开心起来,难得骂人,毕竟我工作以后,起码钱不是那么咬手了。还有就是奶奶受到了来自别人的久违的热情,这个对奶奶来说尤其难得。奶奶感冒的时候,寄住在奶奶身体里的病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班一班的人前来探望,临走说一声:“幽幽到我家玩儿去啊!”奶奶感动的要命,每每热泪盈眶。有时这声音在我耳边跟“贪污犯的孙女”形成交响,面前并不动人的笑容跟记忆中煞神一样的黑脸产生奇异的画面效果,所以我一般只是看着说话的人,并不回答。 后来统计了一下,凡是跟奶奶特别显示友好,对我特别亲切的,他们家里无一例外地都有着一至两个年龄相仿或略大于我的儿子。
单位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娱乐性的联谊活动,但是山城很小,青年都是从小玩到大,互相间感觉没有什么吸引力,活动起来也不太有气氛。好在山城虽小,却住扎着一个海军的雷达基地,那里有一群让山城人多少有点神秘感的军人。 张文就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五四活动的那晚第一次看到张文,只是一眼,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就让我无来头地产生痛楚。那么剽悍的一个身架,相距那么远的站着,一股冬柏的气味,暗浮过来,我能确切地感知那是他的体味。我感觉似乎相见过,并和他有过肌肤之亲,这个感觉应该是荒谬的,我绝对不会认识他,更不应该和他有过曾经。但我就是有那么强烈的寒毛凛凛的感觉,这让我几乎窒息。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我前面的感觉,我今生必须和他有故事。我第一眼对他产生的感觉并不是无来头的,这个身架这个面容我确实看了无数次,他就是抱着小时侯的我照相的年轻军人。十多年过去,但是除了显得老成之外,跟照片上十八岁的哥哥没有大的变化。这个雷达基地归属于他所在的部队,他到这个基地是因为要提升,下来挂职锻炼。本来我要唱一首歌,他用电子琴伴奏,突然停电使活动无法继续。但我和他却频繁约会起来,我很顺口地叫他张文哥哥。在我备尝白眼的成长岁月里,只有照片上的这个哥哥一如既往地朝我微笑,永远那么紧紧的搂着我。我很冷很冷的心颤抖的时候,他的手臂身体透过那不厚的纸张传导给我熏熏的热量。我已经对这个微笑和身体做过无数次抒情的想象。 第一次的疼痛在冬柏的强烈气味和他的温柔里显得微不足道。我的身体蒲丝一样柔软,湿润芬芳,他指尖过处,一路花开,我沉醉他的每一点触及和细碎的喘息,一次次的交融都象仲夏的夜空深邃而旷远,我娇艳盛放得如同午夜的胭脂花一样充满激情。他流着泪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他一定会离开我,这点我从来就清醒地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会这样离开,我必须跟部队的领导承认是我企图勾引他,而他一直在规避我。因为他是军分区副司令的女婿,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允许他对副司令女儿不忠贞。副司令在这个雷达基地的眼线洞悉了他跟我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最后终结必须有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张文期期艾艾拐弯抹角的表示着什么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由苍白憋闷到满面通红。我阻止了他在脑子里继续搜索那些困难的用词,我已明确。有一瞬间我想请赏这张通红的脸一个耳光,但我没有,我做不到对这张十几年来独一无二对我微笑的脸下手。我告诉他,我不会令他的家庭和前程受到丝毫的损伤。我是笑着一字一句的跟他说的,他嘘了一口气,而后流下了眼泪。 发现怀孕的时候张文已经结束挂职离开了山城,肚子里日益反常的变化提醒我这件事情的后果并不是我一个人能承担的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感到毛骨悚然,却对此事束手无策。 我假意关节痛,到医院开了好多活血的药,妄图能够让体内的孽块流掉,单位里有个女工怀孕的时候因为吃了猪血豆腐,竟然流产。但这些东西我吃到几乎呕血,却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那个时候在山城,流产是严重的事件,没有单位证明医院不接受这样的手术。 请章钦臣吃饭之前,我犹豫很久。章钦臣是有点腻心的那种男人,就是一般所说的“色”,他总是对女人动手动脚,无论这个女人是徐娘半老还是青春年少,但是他经管工会和生活这块工作,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说服他给我开证明,让我不声不响地到医院拿掉这块疙瘩。
章钦臣对于我请他吃饭,显出极大的热情。他郑重其事的刮了脸换了西装,绑着恶俗的大红条纹领带来到酒店。其实这个山城实在很小,人跟人都是鼻子撞着眼睛地过着,我请章钦臣吃饭,虽然事先跟老板说弄个僻暗的位子,但这要求本身就十分调动人的好奇心,我在位子上坐着的时候,老板不时的转过来看看我面前的空位会是谁来占座。直到章钦臣走进来,老板菜意味深长地缩着脑袋说:“这个位子好,这个位子好。” 章钦臣半瓶啤酒没落肚,就坐到我的身边,把手搂到我的腰上来,喷着浊气问我:“幽幽怎么这么好?请我吃饭?”我忍住恶心拿开他的手,强笑地说:“有事求您啊!”我知道章钦臣有个木陀陀的儿子,一直娶不上媳妇。我甚至想到,如果章钦臣帮我这个忙,我就把自己嫁给他儿子。他听着我的请求的时候,面无表情,我连忙结结巴巴地把这块砝码加上去。但是我错了,章钦臣瞪着两个灯泡一样的眼睛看我,半天,突然发出鸭子般的哈哈笑声。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你愿意嫁到我家?你愿意嫁到我家?”他把身子趴过来,脏黑的鼻孔几乎压到我脸上,仿佛受到我的强烈侮辱,愤怒又咬牙切齿地低声说“你以为我章家会要一个残花败柳?”我浑身颤抖地在他的鼻息下说不出话。 他突然狞笑着把手从我的领子里伸了下去:“哈哈,乳头已经这么大了,我倒是喜欢的。”我竭尽最大的力气,才从他的手下挣脱,我整整衣服站起来,战战兢兢牙齿打架,我说:“章师傅,您有妻子的,不能……” 章钦臣很生气也很傲气的坐在那里,冰着脸说:“随你的便!” 我站在那里,还想求他,但是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要的,我实在做不到。离开的时候,听到章钦臣在身后说:“你考虑好,世上没有后悔药!”我迟疑了片刻,终于低着头走出酒店。
我被开除的那天,奶奶没有骂我,只是在镜子前不断地换着她仅有的几件衣服,我不知道她想干啥,或许是认为那是她的老单位,想换身体面衣服去替我求情。爷爷端着茶缸在灶间闷不做声。我头痛欲裂,回房关门把自己罩进被窝。那个晚上我走出酒店的门口,被风一吹,就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了,脚下的石头剧烈摇动,回头,已是无路。 我被责令写犯错误经过。男女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也是群众舆论最激烈的问题。跟谁?发生几次?何时?何地?什么感受?要一条条详尽描述。他们要的似乎不是一份检讨,而是一本性体历的小说。我写不出来,因此,对我的作风败坏态度强硬的处理结果是开除! 奶奶换了衣服哪里都没去,一根裤带帮助了她。在所有的绝望里,还有一根裤带给了她可以选择死的希望。 奶奶是上吊死的。是被我的不出息气死,也是对自己一生绝望而死。 令人可耻的是,我还没有想到死。我到街边摆起饮食,卖一些粽子稀饭炒面条之类。先我而摆的摊主们,认为我抢了他们的生意而忿忿不平,我的炉子被冷水愤怒地浇灭不计其数次。
日子要过下去。爷爷的腰背越来越弯,常年的低头不语,闭门不出,使得他的头即使在行走时也几乎磕到自己的膝盖。我的肚子越来越大,总希望这个精血幻化的东西,能够给张文托梦,让他记起他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但我只是被吞吐在山城人茶余饭后的牙缝里。 羊水破开的时候,我正在抹着摊桌,“咕嘟”一声,黏乎乎的液体顺流而下,我提起准备着的一个包就往医院跑——其实是移动,因为裤腿精湿,下腹部物体坠压的感觉使我无法快步。医院并不远,就在街道东头的丁字口,待我鸭子一样彳亍到医院的时候,很多人也呼拥在那里要看大姑娘生养。 医生护士都主动地担当着社会道德的卫士职责,对我未婚生养深恶痛绝——而且自己还说不出是谁的种!我在她们鄙视的目光里捧着肚子来回挂号交费,最后医生让我脱掉裤子躺到产床上。肚子已经痛的我张不开眼,但我还是注意到产床正对面窗帘没有拉紧,有些眼睛在那里窥探,我一边解着裤带,一边央求医生去拉上,遭到训斥:“产房光线不够怎么接生?”赤裸裸八叉在产床上,臀部高高地被垫起。听到窗外男男女女哄哄的笑谈声,我紧闭着眼睛,觉得自己不如一只母狗。
窗外的哄闹声,让一个护士不胜其烦,她走过去,“唰”的拉开窗帘,朝窗外骂到:“你们烦不烦?女人都生过的吧?男人没见过老婆啊?” 强烈的光刺激的我几乎死去。 外面的人虽然被骂,却笑的声音“哗哗”响。护士骂完了却忘记把窗帘拉回去。 我几乎死但是没死,我求医生行行好,拉上窗帘。医生冷眼翻我一下:“拉什么拉?你反正又不要脸!” 那个护士来给我处理体毛的时候,门外有人叫她,她放下剃刀就走了,窗外有笑声调侃:“哇嗬!跟马天民剃头一样呢。” 我知道马天民是电影《泰果隐的秋天》里的好警察,剃头剃了一半就去为人民的鸡毛蒜皮服务。现在护士给我处理一半就走开,令人联想起电影里好笑的情节了,当然直观之下人们觉得这里的情节更精彩。 他们中很多人应该是我的父辈! 我在层层围睹众目睽睽之下生出了我的女儿。因为难产,我被不知死活不知疼痛的剪了一刀,又缝了十一针。 抱着女儿回家的时候,一路上人声鼎沸:“看泰幽幽啊,这年头会骚就叫‘情幽幽’啊!看‘情幽幽’下的野种啊——” 走进冰凉浸浸的家门,爷爷无言地看着我,良久,从不出门的他出去买了一包红糖回来,木手木脚的要给我煮鸡蛋。我放下女儿,接过手自己煮了两碗红糖鸡蛋,跟爷爷吃起来。 没有眼泪。 再去摆摊的时候,我挑着箩筐,一头是食料,一头是女儿。经过这么精彩的生养,看到的自然再三咀嚼其味,没看到的在遗憾中不放弃围观我和女儿的初次亮相。 我被围的水泄不通。我也没有放弃在围观中做生意,很多人一边围观我一边也买了我的粽子,喝了我的稀饭,然后满足地去上班,不上班的也很有兴趣在我的摊边停留。一整天,我的生意好的不得了。 第二天,我还没到,摊上已经围了好些人,我走近的时候发现我的碗柜上贴了一张画,大家的欢声笑语无异于看到土豪劣绅游街戴高帽。 一张奇丑无比的裸体女人像!两个肥大的乳房各用一条线挂着一只破鞋,下体竟然是一只张开的蚌——四周长着乱丛丛的黑毛! 虽然我已经麻木得不知疼痛,但那瞬间我还是震怒了,我放下担子,发疯一样扑过去撕那张画,但也是瞬间边上的几个摊主一起冲上来打我,揪住我的头发,扇我的耳光,大声骂我:“破鞋!破鞋!”我想回手,马上有好心人抱住我的身体,拉住我的手劝:“算了算了!别打!别打!”似乎无意地在下面暗暗地踢了我几脚。 我被打得光赤了上身,裤子也撕破了,鼻青脸肿的我听到女儿在箩筐里的哭声。 裸体画又贴上来,每天我就在画下做着生意。我不想再撕,也不想再打。好象那张画是我的广告。 派出所的老王每天到我摊上喝粥,有时候眯着眼看着那个画,有时候呵呵的冲我莫名的笑笑。有一天他喝着粥问我:“那画你干吗不撕了它?”我看着他,冷冷地说:“没力气!没神气!”一个上学的小孩说:“她不敢撕,撕了要挨打。”老王歪撅着嘴,看看边上暗笑的摊主,若有所思地点着脑袋,走上去撕下那张画,大声地吆喝着说:“以后谁也不许贴广告啊!影响环境美观,谁贴罚谁款了啊!”
被打破的地方还结着痂,我又被章钦臣的妻女呼拥而来痛打一顿。因为我是计划外生育,开证明流产的规定跟计划生育的政策相悖。章钦臣因为是主管被撤了职,章家认为是受了我的祸害。 女儿多多在箩筐里大起来。会说话了。 人们又找到娱乐的新方法。他们会边喝粥吃粽子边逗女儿:“多多,你家里有没有破鞋啊?”女儿就说:“有啊,我妈妈脚上穿的就是破鞋!” 人们很肆意也很满足地放声大笑。他们因此很快乐,我也并不伤心,女儿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保持沉默。 军人是天生要被人崇敬的,某天,几个军人在街上走过的时候,女儿眼睛发亮,尖声大叫:“解放军叔叔好!解放军叔叔好!”我顺着声音望去,其中一个军人正侧过脸去,仿佛街那边有什么吸引了他的视线,虽然他骤然加快了步子,但我还是从那个侧影认出来,那是张文! 他不想让我看见他。 华强来我的摊上喝粥,我才知道他已经被刑满释放了。不过我并不关心,我只是知道他从小顽劣,喜欢打架,也没少欺负我。他原来已经工作,却为朋友把人打成残废进了监牢。 他坐下的时候,多多正坐在小板凳上挑花线,我给他端粥过去,他的眼睛停留在多多灵动的手上。又有人开始每天不厌的娱乐了:“多多,今天你妈妈穿破鞋了没有啊?” 我听到“砰”的一声,一回头,看到华强已经把问话的人打得捂住半边腮帮,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华强眼光凶狠地骂着:“人家已经惨成这样啦,你狗日的还欺负人,对小孩子喷粪!你他妈的太缺德!”他说时手脚不停,把那人一顿痛揍!那人粥也不喝就跑,华强冲他后背吼去:“今天老子揍了你屁开花了,你到老派去告好了,老子我班房娘舅多,再去也不怕!” 华强从此天天来摊上喝粥,喝完了他也不走,就在摊上坐着,他在,没人敢拿多多做娱乐,他也帮我做些提水换煤之类的事情,我也不拦他。他的家里人对他的行为向来是视而不见也无可奈何的,所以没人来找我的麻烦。 一个秋夜,风烛残年的爷爷捧着他那缸茶,突然垂头逝去,没有任何死亡前的痛苦,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轻松的一刻。华强帮我料理了爷爷的后事,顺理成章,在爷爷走后,他搬进了我的房子。 在人们的眼里华强是流氓,我是荡妇,道地一对狗男女。但是狗男女鸠合在一起,由于流氓的煞气,倒是成了山城的太岁,谁也不敢来动土了。我由衷的觉得,在这世上,做个流氓真好! 后来山城造了一个很大的水库,山城的一半成了湖泊,原来的山变成了湖泊中的岛屿,这里又成了旅游区,很多外面的人涌进来,山城好象蛰伏的蛇被隆隆雷声震醒,几乎一夜之间空气都变的躁动不安分了。 人真是善变,祖先两栖动物的天性在极短的时间里,被重新发挥的淋漓尽致。原来的山民,竟然很快成了渔民,很多人做起了水库的生意。女人们原来包裹得密匝匝的躯体,越来越大面积的被开发裸露出来,象互相挤兑着的鱼,肉感地游动在街上,冒着欲望的泡泡。许多年轻人不安于本地生活,纷纷出去闯世界。 街上不时能看到一些妇人手里抱着或牵着没有父亲的外孙,这些都是她们的女儿打混世界的副产品,已经没有人会对这种产品感到稀奇了。 华强跟我同居后,本来是踏三轮车,水库造好以后就买了一艘小船经营旅游客运,私人客运没有被明文允许,但是也没有被严厉制止,只是每月需要以罚款形式交点钱,但是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华强的死应该是他自找的,连累多多死得很冤枉。公家一艘小客轮突然起火的时候,华强正送了一船客人到湖心岛,自己空船回岸边,湖上火光骤起,只听到哭叫声一片,有人开始跳水。所有其他的船只都不敢靠近,华强却加大马力靠过去,火船上的人都过到华强船上来,水里还有人在扑腾,华强跳下去救人,那个落水的人很重也很笨拙,在华强把他托到船边的时候,竟然又滑下来,一屁股坐到华强头上,筋疲力尽的华强冷不防被他一坐,沉到水里去了。多多那天正好跟在船上,扒着船沿看叔叔救人,看到叔叔落水,急的伸手哭喊,船身倾斜,加上人多拥挤,多多也落水了。三天后打捞上来,两个人都全身鼓胀面目全非。 丧事是公家出面料理的。华强是救人而死,要不要树立成典型,扯皮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认为华强是个劳改释放人员,又是无证经营户,树立这样的典型社会效果不好,给了两千块抚恤金,料理了一大一小两具尸体。 焚烧的纸钱象黑蝴蝶一样在风里飞舞,我在坟前痛哭,几个料理丧事的公家人轻描淡写的劝着我:“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哭的太伤心!”后面看热闹的人群里有嘁嘁议论:“还不是想跟公家赖点钱!一个姘头男人,一个偷生的女儿,有什么好伤心?”是的,我还有什么好伤心?伤心又有谁来管?我的眼泪流给谁来看?我猛然一下踢翻烧纸的瓦缸,大笑痛骂:“死了好!死了好!”我笑着大声问站在边上的几个公家人:“是不是死了好?活着也是一世的劳改犯!是不是死了好?我的女儿有我这样的母亲,本身就是罪孽,以后的下场不会比我更好,是不是也是死了好?”我咚咚敲着墓碑:“记住给我安生躺在土里,这死路本来是你们自找的,既然去了就不要想着回来,千年百世不要再出来投胎!”我拍手捶胸跌足大笑,泪水飞溅了一地。
“最毒淫妇心啊。”现在人们终于验证了这千古不变的真理,亲眼目睹一个荡妇对刚刚入土的尸体的诅咒。人们满意地叹息着散去:“老古话说的真是不错啊!” 上天! 当有一天,爷爷以前的那个领导颤巍巍的站在我的面前叫我带他到爷爷坟上去忏悔的时候,我是冷漠的,我收拾不起一点点的同情心,可能我的脸上还露出一点笑吧,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几乎要跪下来,他用老迈的哭声求我,说他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上,求我放他一马。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能力握有别人的生命,我的经历使我对他的这句话感到讽刺,我笑出声来。 这个领导当年威风八面盛气凌人,爷爷是个谨小慎微的会计,虽然算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但年轻的人一个个跨越式地成了他的领导,其中包括在我面前哀求的这一位。是他,当初要爷爷做几笔假帐,胆小的爷爷因为不敢而拒绝,这当然是蔑视和不服从了。爷爷的开除材料写的真是恰当,我嗬嗬笑出声来。 人老了总是要病,病了更加怕死,尤其象这位领导,可能一辈子没有体会过如此切身的悲哀吧?他得了糖尿病,以为自己会死,胡思乱想不知道转到哪根筋,想起当年那么对待我的爷爷,可能犯下了罪孽,为了求得良心和身体上的解脱,竟然一个人偷偷地到山城,簌簌发抖地来求我带他去清洗他的心灵。心灵!他是这么说的,嗬嗬,好笑! 我告诉他,世上没有罪孽,你不需要解脱。我没有带他去爷爷坟上忏悔,我是一个已经没有心肝的女人。 家门口的苦楝树在霏霏淫雨里落了一地的楝花,除了粗暴狂野的脚印践踏而过,并没有人给予一丝回眸。 我开始失眠。我已经很多年不会失眠,就是华强和多多的死,我也没有在夜里睁过眼睛,午夜里曾经有什么星星在眨眼,曾经有什么花儿在怒放,我早已不再去回想。但是,没有出息的,我竟然在多年以后,在风过树梢的的夜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气味,有蚂蚁噬骨的痛楚纠缠我,我在思念一个人! 我没有理由思念那个人,在我走过的路程里,他曾经是胭脂花边一汪泉水,胭脂花曾经为他的柔情疯狂地怒放。但是这汪泉水并没有作为曾经花开的印证存在,他在花残的时候汽雾一样消失。 负情是他的名字,我没出息的泪水竟然为这个名字在夜半滂沱…… 很多的外来人口涌进山城,山城不断扩建,使得这个眼睛撞着鼻子过日子的山城非凡喧嚣,街上来往着很多的生疏面孔。当他踮着脚跨过嶙峋的砖石走进我的院子的时候,我仿佛是看到前生做的一个梦。但这只是瞬间的感觉,因为梦里不会有别人,而他的身后跟了很多人,他是确确实实来到我家,这是第一次。 他离开部队,担任这个新的县级市的副市长,而我在他进门之前不知道他就在本市。 他来视察拆迁现场,这里只剩下我没有搬走,我无处可迁,我所有的积蓄只能买一张床的面积,但是没有任何建筑有这么小的规模。开发公司已经几次派人把我的东西扔出门外,晚间我又一样一样一件一件搬回来,我不知道这样相峙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任何后果都无非是我露宿街头。 他显然没有料到在这样的场合遇到我,他是楞住了。 他叫了一声:“幽幽!”竟然还是多年前一样温柔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已经磨砺得坚硬如铁,但是这一声还是雷霆一样打中了我,我几乎站不住,我用后背紧靠着院墙,尽量让自己站直,我的心骤然地酸痛,几乎落泪。 只是瞬间的温柔。他似乎怕我开口,匆匆告诉我必须在三日内搬出,说了几句体谅政府工作的难处,配合开发公司建设新城市之类,急忙忙的就转身离去。 看着他的脚步跨出院门,我的泪水山洪一样淹来,我追出去:“我们的女儿,她已经死了。我嫁了一个老公,是个劳改释放分子,也死了。” 他没有回头。 跌到在小车卷起的尘烟中,我放声地大笑,我为什么流泪?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为谁九断回肠?就象多年前那个停电的夜晚,有一首乐曲在我的生命里永远不会响起来,谁会来体恤我今生的苦和痛?谁会为我做一次的回头? 苦楝花在我的笑声里簌簌狂落。 一个人活着,我无家可归,从肉体到心灵,没有收藏,也没有掩藏,人家说我疯了,但我知道,上天没有那么慈悲,我没疯,我要重新活一次,从那以后,我开始捡破烂,买废品,好在,这个社会还有我的容身之处,由于我胆子大,2年就开了第一家废品收购站,接着是第二家...,15年后,开了10家废品收购站,还有了3个水站,我有了自己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事业。每当我开着路虎路过这条我曾经住过的街道,总是让我五味陈杂。我,又活了一次。